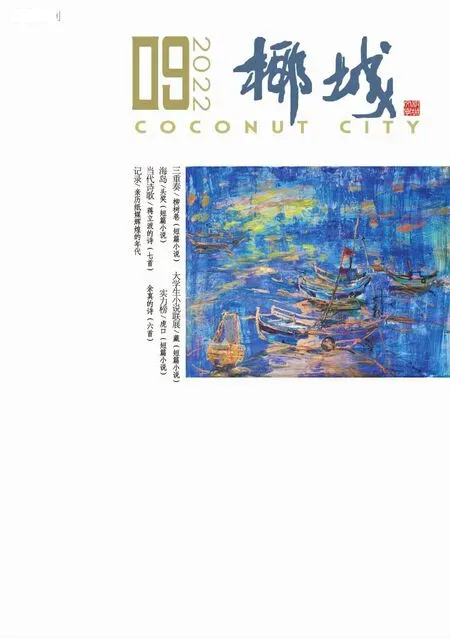母親的房子(五首)
陳年喜
苧麻
1978年的峽河兩岸
種滿鋪天蓋地的苧麻
社員們露著屁股除草打枝
據(jù)說這是制作麻料最好的材料
一些大人物穿著它來華訪問
締結大國友誼
苧麻開花結果的過程
特殊的香氣讓七月迷醉
一群孩子有時上學有時逃學
在苧麻地里打鬧
整個秋天我們和大人一道
剝苧麻皮把它們浸入峽河
無數(shù)的小魚和鳥在臭水里暈死
1999年 苧麻走到了盡頭
峽河兩岸替換了鋪天蓋地的核桃
一些事物的消逝連手勢也不會留下
這當然并不奇怪除了刀光劍影
誰也沒有在往事里找到過往事
最后的苧麻被搓成了繩子
捆綁犯事者和柴草
村西的鈴鐺借一棵樹丫
用它了結了十七歲的青春
武峰山
民國六年一個
叫蔣師傅的道士在此落腳
三年后他用行醫(yī)的積蓄
建起了一座磚石寺廟
在此之前人們叫它武峰山
從此之后人們稱它武峰廟
山河有命運
而更多出于偶然
山腳的峽河沒有這樣的幸運
還一直被叫作峽河
三十年河東四十年依舊河東
而它流經(jīng)的時代
已幾度拐彎
一百年后我來到這里
松林還是那片松林
松濤已經(jīng)換了頻率
鮮花寂寞的坡地上
埋著早已被人遺忘的游醫(yī)
和他救人無數(shù)的手藝
從這里可以望見丹江
望見它流過早已失去意義的武關
地理的意義從來沒有意義
麻雀飛過北面的青岡林
消逝于可見的天際
母親的房子
母親的房子土坯所壘
在2018年的鄉(xiāng)村拆遷中夷為平地
如今我們在上面種了紫色豆角
一種保留了三十年的品種
瘦弱的豆蔓努力上升絕不回頭
豆角有豆角的法則
它并無意代表曾經(jīng)的主人
鋤刃是雪亮的
但鐵有遺忘的屬性
它只負責讓土歸于土
早已忘記靠東的角落
是一張多病的床
靠西的門邊是一張桐木柜子
而在南面有一只木格柴窗
床上的人每天借以眺望對面山上的雨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房子
我現(xiàn)在居住的房子是三間磚木結構
比母親的房子顯得高級
在院子被拆掉的前一天
我讓弟弟拍下照片作為最后的記念
圖片中的兩座房子一明一暗
土坯房子在晚霞中靜靜回家
像每個時代的落幕
顯得真實又委屈
豆角會在六月開花
七月結出繁密的果實
如果那時候你正好路過
我愿意捧上一捧給你
這是唯一同質(zhì)于母親的食材
和土豆同煮的湯
不放鹽也可以食用
峽河久旱
從二月到現(xiàn)在
峽河一直久久無雨
這是往年少有的年景
山峋水瘦是一個好詞
但只適應于文人
病態(tài)的喜好
記得一九九八年
曾有過相同的情景
那一年的麥子顆粒無收
我們一群青年去采石場打工
七月初八下了一場透雨
我們從山上回來
去時十八人回來剩八雙
早上給豆角澆水
從開始的每棵兩瓢減到半瓢
清冽的井水映照過豐收
也映照過欠收
每打出一桶水面會落下去半尺
歲月的苦澀它比我們先知道
寫一首詩是容易的
難的是對于歲月
剔除多余的輕佻
不是所有的生活都是生活
只有明天不舍晝夜
豌豆的香氣
愛人在廚房炒豌豆角
在裝盤時豌豆的香味
充盈了整個院子
我正好從地里回來
一身露水一同見證了
這莊重的時刻
經(jīng)過高溫炒過的豆角
依然保持了青綠的顏色
這是寧死不屈的食物之一
云貴人喜食豌豆的芽尖
而四川人喜歡用它炒臘肉
在寸草不生的喀喇昆侖山一角
我曾親見過它們把干燥的生活
過出大巴山的氣色
豌豆的采收季節(jié)就要過去了
園子里的豆秧就要讓位于他物
因為久旱它們比往年提前退場
一個無雨之夏對于一些植物
就是一個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
但芽尖依然開滿白花
我想那一定是尊嚴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