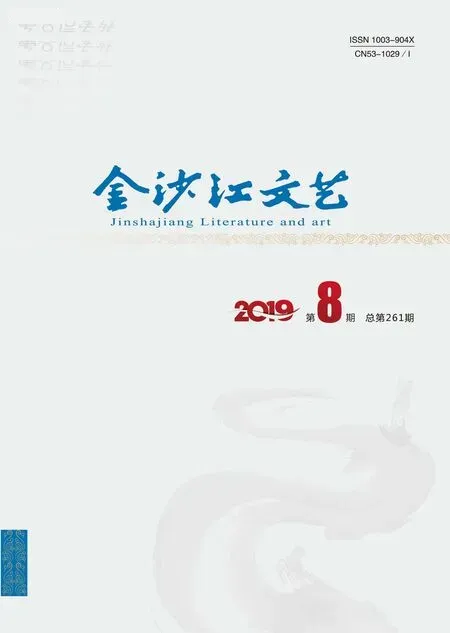千里孤岸的詩
◎千里孤岸
如果詩人思考每一個(gè)字
詩人手指上能飛出十只蝴蝶
若他愿意 但憑體力
拿長篇小說壘墻 種些彩色小短詩
他可以經(jīng)營好一個(gè)皇家花園
若愿意放蝴蝶們飛來飛去傳播花粉
他就能不費(fèi)吹灰之力
成為一個(gè)好園丁 做另一個(gè)克盧修斯
若他愿意 他可以學(xué)歐陽修 彼特拉克
或特朗姆特羅斯 用蘆葦桿 用鵝毛筆
或者打鍵盤 詩句會(huì)從江西的沙上
從墨水瓶中 或電腦主機(jī)出來
古往今來 詩歌的第一題材是大腦
如果一個(gè)詩人思考每一個(gè)字
大腦靈活一點(diǎn) 作為身體的一部分
它將在紙上開展機(jī)械運(yùn)動(dòng)
物理運(yùn)動(dòng) 化學(xué)運(yùn)動(dòng)或生物運(yùn)動(dòng)
它不斷蹦出字來如黑芝麻的爆米花
字與紙之間 一改再改 改了又改
詩歌將三次以上復(fù)制靈魂
夢與醒之間 以假如記憶可以移植
為主題的詩歌比賽三天前
詩人可以重新懷孕詩句
酒與醉之間 收信者若清早拆閱來稿
詩歌信件會(huì)展開雙手推開玻璃窗
放新鮮空氣進(jìn)屋 然后雙手變雙翅 飛去花園
我在世間數(shù)數(shù)
我在世間數(shù)數(shù) 第五是紅的
起承轉(zhuǎn)合之后 另一個(gè)我去幫我行走
三五年的冬天他都穿紅色大衣
讓滿天空的雪無地自容
直到今年我在玻璃山抓住那個(gè)我
他的色彩終于有所收斂
但他拒絕回到我內(nèi)部
我強(qiáng)迫另一個(gè)我 如用一塊肉體打空靈魂
我數(shù)著數(shù)字 用阿拉伯傳過來的口吻
他拿到過冰島的右腿離開我
試圖用兩個(gè)人都喜歡的亞熱帶方式
我不是星期五 你不是魯濱遜
他大聲叫喊如土著 流浪多年
他講故事的顏色由黑化作蒼白
無力打動(dòng)一只獨(dú)木舟
那長身軀的舟子曾經(jīng)行過撒哈拉和剛果
第五年負(fù)傷 借自己血液流淌至今
把擱淺當(dāng)做命運(yùn)不是一條好船
那條1967年誕生在小說里的除外
它骨架仍在 被馬爾克斯稱為西班牙帆船
然而西班牙 西班牙
不是一顆含鈣元素的撕咬工具
在充滿海水的大航海時(shí)代
它們盡是無敵之物
直到我拿手指跨過英吉利海峽
一下子數(shù)到倫敦
這個(gè)曾經(jīng)的世界第五大首都
人口八百萬卻一直孤獨(dú)如另一個(gè)我
虛度年華 白白打了2000年的大笨鐘
世界地圖
世界地圖是地球最大的一幅肖像 是最美的畫
青藏高原 亞洲最高昂的頭 白發(fā)蒼蒼
里海是腎 黑海是心 地中海是大象
鼻尖在直布羅陀 歐亞兩根繩子
結(jié)頭處在伊斯坦布爾 那地方古時(shí)候叫拜占庭
更早是東羅馬首都君士坦丁堡
古羅馬如今叫意大利 是一只長筒皮靴
腳尖為西西里島 歐洲最碎
英國形象完整 是一只偷東西逃跑的兔子
偷的東西是愛爾蘭
非洲像一只地球的左肺
因?yàn)槌榱嗽S多年草煙 非洲給人印象是黑色的
澳大利亞四方被咬 是世界上最吸水的一塊面包塊
太平洋在最初畫地球時(shí)是藍(lán)色畫板
加拿大是畫家最早用來調(diào)色塊的地方它右上角呈棉絮狀
美國船在上 用墨西哥做錨 鉤著拉丁美洲
加勒比海撒滿小島做魚餌
亞馬遜河水流出一把扇子 巴西胖成一個(gè)黃芒果
智利是瘦腰的男子
是整塊美洲雄性大陸的腰部骨頭
來龍去脈清晰 直到冰的南極
一朵雪靈芝長在地球深處
米開朗基羅在石頭之內(nèi)
在西斯廷 米開朗基羅的脖子硬邦邦
教堂天花板花里胡哨 世界在七天齊備
他把七天的故事畫完用了四年時(shí)間
在高度超過寬度的石頭盒子里
他仰面朝天作畫 鼻子頂著萬能之主
他的那只鼻子 十四五歲時(shí)被人打過一拳
他一生都認(rèn)為他鼻子里有一根骨頭
是塌陷的 他相貌平平 不帥不怪
與他所有的男性雕像相比 他是自卑的
直到主持修建圣彼得大教堂
他還在尋求一種暗中補(bǔ)償
他把教堂圓頂突出于羅馬大地之上
繪畫和建筑之外 作為詩人的米開朗基羅
第一和最后的榮光都在石頭之內(nèi)
他是脾氣暴烈的雕塑家 從寄養(yǎng)的石匠家里出來后
他一生都忘不了打石頭 他攻擊他的每一件作品
用錘子和刻刀 他把一種痛苦之力注入大理石
像他寫詩時(shí)把動(dòng)詞注入所有名詞
那些石頭裹著肌肉與骨頭 是熱乎乎的尸體
封閉了不安的動(dòng)感 在最后一錘砸下時(shí)
那些尸體渴望再來一錘子 砸碎殼子活著出來
如此說來 他更像一個(gè)兇手 拿石頭去固定運(yùn)動(dòng)者
使其終身監(jiān)禁 例如在白色大理石中
大衛(wèi)至今未投出石子 摩西的怒氣止于抓胡子
圣馬太只擠出右手 左腳和他的三分之二毛腦袋
皮影戲
對(duì)白少 有一種孤獨(dú)是一個(gè)人的話劇
一個(gè)人演主角和配角
如荒野小學(xué)里一個(gè)人既是校長又是門衛(wèi)
白天既要教書又要淘米洗菜
晚飯后才能自己演個(gè)小戲
舞臺(tái)在黑的風(fēng)上 照明的蠟燭東倒西歪
四個(gè)角熄滅了三根 幕布逆風(fēng)發(fā)抖
夜晚太深 連惡作劇的觀眾也沒有
用旁白的方式 喝個(gè)倒彩吧
希望隔墻有耳
我把雙手湊近唯一燭火
無意中比出了一只巨大的黑耳朵
一把跳舞的鉗子咬我
“讓很多誘人的舞蹈/把瘟疫傳到全城里去”
——(英)威廉·布萊克
當(dāng)年我能歌善舞 很小就是音樂的神
我的舞蹈有車之雙輪 我的歌聲有鳥之兩翼
我身后有一個(gè)世界跟著狂歡
大家都走起了太空步 都用上了機(jī)械手
據(jù)說那些深夜僵尸們都會(huì)護(hù)著襠部舞蹈
我又喜又瘋 我在人生最淺的地方尖叫
用尖頭皮鞋拼命踢踏玻璃鋼舞臺(tái)
又把皮鞋拋向臺(tái)下的閃光燈
據(jù)說眾人為爭一只皮鞋還叫來5輛警車
我又黑又白 仿佛皮膚上涂滿兩個(gè)大洲
而實(shí)際上所有大洲我都去了
包括到南極教帝企鵝跳舞
我從海洋上空飛過一年四季
波音787帶我去到眾多國家傳染
我忘乎所以 不記得來自印度還是埃及
我像一個(gè)瘋狂的病菌游蕩在地球
直到最后一次樂極生悲
那天我在一個(gè)廢棄的兵工廠演出
有人裝成后現(xiàn)代派的工人伴舞
我裝扮成一顆吃了搖頭丸的螺絲釘
在我手中跳舞的一把破壞鉗咬我的右手
如鱷魚之口咬斷一節(jié)甘蔗 我用歌聲尖叫直到昏死
三個(gè)月后我裝了假肢
從此上臺(tái)我戴上了黑手套 只唱不跳
我用兩只話筒 左邊唱歌 右邊講假話
語言的家
語言的家中應(yīng)該有個(gè)詞語噴泉
一塊水變幻多端 灑出的句子出神入化
大廳里那些精神的影子反射彩色
走廊寬闊 廊柱玲瓏 陽光從玻璃飛進(jìn)來
如透明蒼蠅穿過一道道空氣 靈感振翅
屋里閃光的骨頭生長 骨頭上掛滿小巧思
仿佛剛剛過了一場東方圣誕 古典之樓下
院子里滿地泰戈?duì)栭_放 爭先恐后
它們汁液飽滿 炸開的濃香傳出很遠(yuǎn)
把四方的漢字都吸引了 這些漢字太熱鬧
喜歡三五成群組成專有名詞 形容詞和動(dòng)詞
它們坐過9個(gè)站臺(tái) 從一首詩中下車
最后集體擠在雕花鐵欄門外等著通傳
語言的家中主人是一位孤獨(dú)的古典詩人
他深居簡出 很少澆水 詩歌四季黑暗
他讓仆人把那些黑漆漆的詞都轟走了
入夜時(shí) 他躺在院子里濕的土上 一個(gè)人說話
那些秘密語言朝著天空幸福 整個(gè)晚上
發(fā)芽 開花 結(jié)無花果